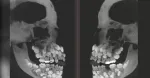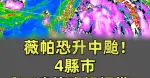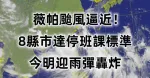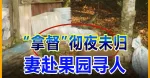趁著女兒去參加暑期夏令營,我決定給她一個驚喜——徹底清理她那堪比「二戰現場」的房間。
過程如同考古發掘,從零食包裝袋到寫滿歌詞的草稿紙,應有盡有。
就在我擦拭書架頂層時,一個巴掌大的小鐵盒闖入視線。
它被藏在一堆舊課本後面,蓋子上還貼了一張便簽,畫著一個可愛的笑臉。
「小丫頭,還藏秘密基地呢。
」我笑著嘟囔,好奇地打開盒子。
裡面的東西卻讓我瞬間皺緊了眉頭。

那是幾個由乾枯植物編織成的「小人」。
它們造型極其怪異:主幹是一根細長堅硬、帶著明顯一節一節凸起的草稈,頂端巧妙地用草葉打了個結,像個小腦袋,兩側還分出兩根更細的草稈,仿佛張開的手臂。
整體呈現出一種枯黃、原始,甚至帶點神秘詭譎的氣息。
我的第一反應是頭皮發麻。
這看起來太像某種……無法言說的古老儀式用品了?
青春期的孩子到底在接觸什麼稀奇古怪的東西?
各種不好的猜想瞬間塞滿大腦,擔憂和一絲恐懼讓我坐立難安。
我不敢直接問她,怕貿然質問會破壞我們之間難得的信任。
糾結再三,我選擇了一個自以為聰明的方法。
我選了一個最完整的「草人」,把它放在書桌上,找好角度拍了張光線充足、細節清晰的照片,避開任何能顯示房間背景的線索,然後發布在一個成員背景非常多元的社交論壇上。

我的配文充滿了老母親的不安與困惑:「求助萬能的網友!在娃房間裡發現這個,是用乾草編的,造型有點瘮人。
這是啥啊?
有沒有懂的給科普一下?
老母親心裡有點慌……」帖子發出後,我隔幾秒就刷新一次,心跳加速地等待著回復。
最初的幾條和我一樣,表示「看不懂」、「有點詭異」。
但很快,畫風就變了。
一位IP位址顯示為陝西的網友率先留言:「哎喲!這不是節節麥嘛!阿姨,您女兒手真巧!」
節節麥?
我正愣神,後續的回覆像潮水般湧來,瞬間淹沒了我的擔憂。
「哈哈哈哈,阿姨您別怕!這是我們小時候在麥地里最常見的野草,學名好像叫『節節草』,稈子是一節一節的,特別脆,一拔就斷,聲音清脆好聽!」「破案了!這是80、90後的童年回憶啊!放學路上就愛拔這個玩,互相比賽誰拔得響。
你女兒居然會用它編小人,太有創意了!」「阿姨,您女兒不是中了啥邪,她是找到了我們童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啊!這手工,沒點耐心還真編不出來,厲害!」

「淚目了!沒想到現在的孩子還玩這個,我以為他們都只認識手機呢。
您女兒是個懂得生活趣味的寶貝!」一條條充滿懷舊和歡快的評論,像陽光一樣驅散了我心中所有的陰霾。
我拿著那個小小的「草人」,再次仔細端詳,它的形象徹底變了。
那不再是什麼詭異的神秘物件,而是一個精巧的、充滿童趣的手工藝品。
我仿佛能看到女兒坐在書桌前,小心翼翼地整理著這些乾枯的草稈,專注地編織著,或許是在回憶某次郊遊的見聞,或許只是想做一個獨一無二的小擺件。
巨大的愧疚感和一種難以言喻的欣慰同時湧上心頭。
我愧疚於用自己世故和焦慮的視角,去揣測女兒純粹的世界。
而我更欣慰的是,在這個被電子螢幕包圍的時代,她依然保有一份對自然細微之物的好奇與耐心,擁有一種我無法理解的、安靜的快樂。
我沒有回覆任何一條評論,只是默默地把那個「節節麥小人」小心翼翼地放回鐵盒,擺回了原處,仿佛從未動過。
但我知道,等女兒回來,我不會再盤問她的小秘密。
我會和她聊聊我的童年,然後,真誠地請她教我,怎麼才能編出這麼一個可愛的小人。

 荊倫風 • 2K次觀看
荊倫風 • 2K次觀看
 劉奇奇 • 2K次觀看
劉奇奇 • 2K次觀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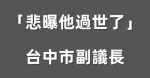
 武巧輝 • 5K次觀看
武巧輝 • 5K次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