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塊上好的漆板,需經歷上百道工序,才能在幽暗中沉澱出溫潤的光。
一個姓氏,承載的又何止是一個代號。
它是一部家族史的索引,是血脈流淌的河床,是無數個除夕夜裡,晚輩對長輩磕下的那個頭。
當我的兒子,帶著一個隨母姓的孫女,站在我面前,張嘴就要掏空我半生積蓄時,我才明白,有些傳承,比金漆脫落得更快,有些河床,早已乾涸龜裂。
01

南城的六月,潮熱得像一塊擰不幹的毛巾。
院子裡的老槐樹無精打采,連蟬鳴都帶著幾分黏膩的煩躁。
我正用一方鹿皮,慢條斯理地擦拭著工作檯上那件剛上完最後一遍大漆的紫檀嵌螺鈿小盒。
光線從雕花木窗透進來,落在盒面上,流轉出深海般變幻莫測的光暈。
這活兒急不得,得像對待初生的嬰兒,力道、溫度、心境,差一絲一毫,前面九十九道工序就都白費。
院門"吱呀"一聲被推開,打斷了滿屋的靜謐。
我的兒子陳家輝,領著一個約莫四五歲的小女孩站在門口,神色有些不自然。
他穿著一身熨燙筆挺的商務休閒裝,頭髮用髮蠟梳得一絲不苟,與這間充滿了木料與生漆味道的老屋格格不入。
"爸。"他喊了一聲,聲音不大,像是怕驚擾了什麼。
我沒回頭,目光依舊專注在漆盒上,只是"嗯"了一聲。
那個小女孩躲在陳家輝腿後,探出半個小腦袋,一雙烏溜溜的大眼睛裡滿是好奇和怯生。
她長得很秀氣,像她的母親林嵐。
只是,她叫林念。
隨她母親的姓。
這是她第一次踏進這個家門。
出生、滿月、周歲……每一次,陳家輝找各種理由推脫,我知道,癥結在哪。
我只有一條規矩,陳家的長孫,必須姓陳。
他們沒做到,所以這道門,他們也一直沒好意思進。
"小念,叫人。"陳家輝推了推孩子。
小女孩怯怯地看了我一眼,小聲喊了句:"爺爺好。"
聲音軟糯,卻像一根細針,扎在我心上。
爺爺?
我是她爸的爸,按規矩,她該喊我姥爺才對。
一個稱呼的錯位,清晰地標明了我的身份——一個無足輕重的外人。
我終於停下手裡的活,將鹿皮巾整齊疊好,轉身看著他們。
我沒理會孩子,目光直直地投向陳家輝:"無事不登三寶殿,說吧,什麼事。"
陳家輝的臉頰抽動了一下,似乎在組織語言。
他蹲下身,對小女孩說:"小念,你先在院子裡看看花,爸爸跟爺爺說幾句話。"
林念乖巧地點點頭,邁著小短腿跑到槐樹下,好奇地研究著掉落在地上的槐花。
陳家輝深吸一口氣,從公文包里掏出一疊裝訂整齊的文件,放在我面前的另一張桌子上,推了過來。
"爸,我跟幾個朋友,合夥做了個項目。AI數字人直播帶貨,風口行業,前景非常好。這是我們的商業計劃書,已經有兩家投資機構表示了初步意向,就差一筆啟動資金了。"
我沒去看那份花里胡哨的計劃書,只端起手邊的茶杯,吹了吹漂浮的茶葉:"差多少?"
"三百……三十萬。"陳家輝的聲音壓得很低,說完這兩個字,他仿佛用盡了全身的力氣,眼神躲閃,不敢與我對視。
我端著茶杯的手,穩如磐石。
三十萬。
對我來說不是什麼大數目。
可從他嘴裡說出來,分量卻重若千鈞。
他知道我這輩子最看重的是什麼,也知道他今天的行為,無異於在我這顆老榆樹心上,再刨上一刀。
屋子裡靜得可怕,只有牆上老座鐘的秒針在"咔噠、咔噠"地走著,不疾不徐,像是在丈量我們父子之間那段難以逾越的距離。
許久,我輕輕地笑了。
笑聲不大,卻讓陳家輝的肩膀猛地一顫。
他抬起頭,驚疑不定地看著我。
我放下茶杯,杯底與桌面碰撞,發出一聲清脆的響聲。
我指了指院子裡那個正專心致志撿槐花的小身影。
"讓她,"我一字一頓,聲音不大,卻清晰地傳到他耳朵里,"現在走過來,對著我,清清楚楚地喊一聲『姥爺』。"
陳家輝愣住了,滿臉都是困惑。
我伸出兩根手指,在桌上點了點。
"一聲『姥爺』,我給你兩百萬。不是三十萬,是兩百萬。"
"你看著辦。"
02
陳家輝是踉蹌著走出那間老屋的。
父親平靜的眼神,和他口中說出的那個石破天驚的數字,像兩座大山,壓得他幾乎喘不過氣。
兩百萬,買一聲"姥爺"?
這聽起來像是一個荒誕的笑話,可父親臉上的表情,沒有半分玩笑的意味。
他牽著女兒林念的手,掌心全是汗。
林念抬起頭,不解地問:"爸爸,我們為什麼不等爺爺一起吃飯?"
"爺爺……爺爺忙。"陳家輝敷衍著,腦子裡亂成一鍋粥。
回到他和林嵐在城東那個裝修精緻的現代化公寓時,天色已經擦黑。
林嵐穿著一身幹練的居家服,正在客廳里用筆記本電腦處理工作郵件。
她是一家外企的項目總監,永遠都是一副雷厲風行、掌控一切的模樣。
"怎麼樣?"她頭也沒抬,直接問道。
陳家輝換了鞋,頹然地坐在沙發上,將女兒攬進懷裡,卻沒有說話。
林嵐終於察覺到不對勁,她合上電腦,走到他面前,眉頭微蹙:"沒給?我就知道。那個老頑固,心裡只有他的那些破木頭和老規矩。讓他拿錢,比要他的命還難。"
"他說了。"陳家輝的聲音沙啞乾澀。
"說什麼了?又拿孩子姓氏的事情說事了?"林嵐的語氣裡帶上了明顯的火藥味,"家輝我再跟你說一遍,小念跟我姓,是當初我們領證前就說好的。我爸媽就我一個女兒,他們不圖什麼,就圖個念想。這件事,沒得商量。"
"他沒提姓氏。"陳家輝抬起頭,眼神複雜地看著自己的妻子,"他說,只要小念當面喊他一聲『姥爺』,就給我們兩百萬。"
客廳里瞬間安靜下來。
林嵐臉上的不耐和嘲諷,一點點凝固,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極度的錯愕和不可思議。
"兩……兩百萬?"她幾乎以為自己聽錯了,"他瘋了?他哪來那麼多錢?"
在林嵐的印象里,她的公公陳望年,就是一個守著一間破舊老宅和一堆沒人要的"老古董"過活的孤僻老頭。
有點手藝,會做些木工活,逢年過節,親戚們會過來討要一兩件小玩意兒,也就僅此而已。
他的退休金也就幾千塊,怎麼可能隨手拿出兩百萬?
"他沒瘋。"陳家-輝搖搖頭,臉上露出一絲苦澀,"他那個人,從不說沒把握的話。他說兩百萬,就一定拿得出來。問題是,他這是在羞辱我們。"
林嵐沉默了。
她是個極其聰明的女人,瞬間就明白了這"兩百萬"背後的深意。
這不是一筆交易,這是一道選擇題。
一邊是區區三十萬的啟動資金,代表著他們孤注一擲的"風口事業";另一邊是兩百萬的巨款,代價卻是要他們在一個稱呼上低頭,承認陳望年在家庭序列中的"正統"地位。
用金錢,來衡量他們夫妻倆的尊嚴和他們給女兒選擇的姓氏權利。
"他憑什麼?"林嵐的聲音冷了下來,"就憑他是你爸?他養過小念一天嗎?他給小念買過一件衣服、一罐奶粉嗎?小念出生到現在,他連看都沒來看過一眼!現在倒好,擺起長輩的譜,用錢來砸我們?陳家輝,這錢,我們不能要!"
"可我們的項目怎麼辦?"陳家輝焦躁地站起來,在客廳里來回踱步,"投資人那邊催得緊,再沒有資金注入,整個項目就要黃了!這幾年我一事無成,好不容易抓住這個機會,我不想放棄!"
他的聲音裡帶著一絲哀求:"嵐嵐,要不……就讓小念喊一聲?就是一個稱呼而已,我們拿到錢,把事業做起來,以後不就有底氣了?"
"一個稱呼而已?"林嵐像看陌生人一樣看著他,"陳家輝,你沒明白嗎?今天我們要是為了錢讓小念改口,明天他就能為了別的,讓我們給小念改姓!這是一步退,步步退!我們的底線就徹底沒了!"
她指著門口,聲音都在發抖:"你爸不是在給我們錢,他是在給我們立規矩!是用錢,在我們頭上懸一把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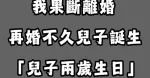
 武巧輝 • 8K次觀看
武巧輝 • 8K次觀看
 楓葉飛 • 4K次觀看
楓葉飛 • 4K次觀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