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枚偽造的馬爾地夫商務艙行程單,兩張早已退票的頭等艙機票,一個被搬空到只剩消毒水氣味的家。
我做完這一切時,天還沒亮。
我那個習慣了妥協與付出的丈夫,將在十二小時後,帶著他那懷孕八個月、準備鳩占鵲巢的姐姐,迎來一場盛大的空歡喜。
他會咒罵我的冷血,他會因為無法向家人交代而急瘋。
但他絕對想不到,真正將這場家庭鬧劇推向深淵的,不是我的消失,而是三名警察的到來。
01

"小畫,你這房子敞亮,又是新風又是地暖,比我那老破小強太多了。就這麼定了,下個月預產期,我就讓你姐搬過來坐月子。"
婆婆用一種不容置喙的語氣,為這場名為"家庭聚餐"的鴻門宴,畫上了最終的句點。
她那雙渾濁但精明的眼睛掃過我精心布置的客廳,像是在巡視自己的領地。
我丈夫陸鳴,坐在我身邊,用手肘在桌下輕輕撞了我一下,眼神里滿是祈求。
那眼神我讀得懂:忍一忍,就一個月,別讓我媽下不來台。
我垂下眼帘,看著面前那盤幾乎沒動過的松鼠鱖魚,醬汁已經開始凝固,像一塊琥珀,封存著今晚所有的荒誕與可笑。
坐在對面的大姑姐姜芮,挺著巨大的孕肚,臉上帶著理所當然的羞怯,柔聲細語地附和:"弟妹,那就辛苦你了。主要是你這裡離兒童醫院近,萬一孩子有個黃疸什麼的,方便。我坐完月子肯定給你包個大紅包。"
紅包?
我心裡冷笑。
她上一次借走的三萬塊,說是給孩子報早教班,至今未還。
陸鳴說,都是一家人,別催。
我的指甲深深陷進掌心,鈍痛感讓我維持著表面的平靜。
這套一百六十平的房子,首付是我婚前的積蓄,是我的婚前財產。
房貸,我們兩人共還,但我的公積金覆蓋了大部分。
從設計圖紙到軟裝搭配,每一塊磚,每一寸牆布,都傾注了我的心血。
這裡是我的巢,不是誰都能來下蛋的收容所。
"媽,姐,"我終於開口,聲音平靜得像一潭深水,"不太方便。"
空氣瞬間變得粘稠。
婆婆臉上的笑容僵住了,筷子"啪"地一聲拍在桌上。
"什麼不方便?你一個搞審計的,又不用坐班,天天在家對著電腦,還能耽誤你什麼事?你姐可是懷著我們老陸家的長孫!你不伺候,誰伺候?"
"我月底要去馬爾地夫出差,一個併購案的盡職調查,要去半個月。"我面不改色地拋出了早已準備好的說辭。
"出差?"婆婆的嗓門拔高了八度,"什麼差這麼重要?比你親外甥還重要?推了!"
"推不了,違約金三百萬,公司不出,我出嗎?"我平靜地回視她,第一次沒有選擇退讓。
陸鳴的臉色已經變得煞白,他不停地給我使眼色,嘴唇翕動,卻一個字都說不出來。
他知道,我說的是謊話。
我的職業是企業內控與風險評估,根本不是審計,更沒有什麼去馬爾地夫的併購案。
但這個謊言,是專門為他們量身定做的。
對他們這種講"情"不講"理"的人來說,只有"錢"才是唯一不可撼動的道理。
姜芮的臉色也沉了下來,她撫摸著孕肚,幽幽地說:"弟妹,你就是不歡迎我。我知道,你一直覺得我們家拖累了陸鳴。可他是我親弟弟,我不指望他,我指望誰?"
這句話像一根毒刺,精準地扎進了陸鳴的軟肋。
他立刻挺直了腰板,仿佛要捍衛什麼神聖的親情。
"舒畫,你怎麼說話呢?我姐來住一陣子怎麼了?你出差,不是還有我嗎?我能照顧!"
我看著他,忽然覺得無比陌生。
他能照顧?
一個連自己襪子都找不到,每天早上需要我把牙膏擠好的人,要照顧一個產婦和一個新生兒?
"你拿什麼照顧?"我問,"你請假嗎?你那個項目經理的位置,不想要了?還是說,你準備讓你媽和產婦、新生兒一起,天天吃外賣?"
"我……"陸鳴被我問得啞口無言,臉漲成了豬肝色。
婆婆見兒子落了下風,立刻重整旗鼓,開始拍著大腿哭嚎起來:"我這是造了什麼孽啊!兒子娶了媳婦忘了娘啊!芮芮,我的兒,你命苦啊,連個坐月子的地方都沒有,婆家嫌棄,娘家弟媳不容……"
姜芮也適時地捂住臉,肩膀微微聳動,發出壓抑的哭聲。
一唱一和,珠聯璧合。
這是她們慣用的伎倆,用"親情"和"孝道"進行綁架,陸鳴每一次都會繳械投降。
果然,陸鳴"噗通"一聲站了起來,雙眼通紅地瞪著我:"舒畫!你今天必須給我姐一個說法!這個家,到底還是不是我說了算?"
我看著眼前這齣鬧劇,心中那根名為"忍耐"的弦,終於徹底崩斷。
好,你們要一個說法。
那我就給你們一個說法。
我緩緩站起身,臉上甚至帶上了一絲微笑,那笑容讓陸鳴感到了不安。
"行,我說了不算,你說了算。"我拿起餐巾,慢條斯理地擦了擦嘴角,"就按你說的辦。姐,歡迎你下個月來家裡住。我出差這段時間,就辛苦陸鳴照顧你了。"
說完,我拎起包,在他們錯愕的目光中,轉身走出了家門。
陸鳴沒有追出來。
我知道他不會。
在他看來,我已經"服軟"了。
他此刻一定正安撫著他的母親和姐姐,享受著作為一家之主的勝利喜悅。
他以為,這又是一次爭吵後的妥協。
他不知道,這一次,是戰爭的開始。
02
離開家後,我沒有回父母那,也沒有去閨蜜家。
我用自己的身份證,在離家三十公里外的一家五星級酒店開了間房。
推開房門,將自己摔進柔軟的大床里,我才感覺到四肢百骸傳來的疲憊。
這不是身體的累,而是長久以來,精神被不斷消耗、邊界被反覆侵犯後的透支感。
我和陸鳴結婚三年。
他是個溫和的男人,或者說,是個軟弱的男人。
在我們的二人世界裡,他體貼入微。
可一旦牽扯到他的原生家庭,他就變成了一個沒有原則的"調解員",而我,永遠是需要"顧全大局"的那一方。
他的工資卡是婚後交給我的,但他每個月都會以各種名目,從我這裡拿走至少三分之一的錢,轉給婆家。
婆婆的養老金,大姑姐孩子的學費,甚至是他家遠房親戚來城裡看病的紅包。
我不是沒有抗議過。
每一次抗議,都會引來陸鳴的懇求和婆婆的哭鬧。
"小畫,我媽養大我不容易。"
"舒畫,我姐從小就讓著我,現在她困難,我能不管嗎?"
"我們是一家人啊,分那麼清楚幹什麼?"
在這樣日復一日的消磨中,我的底線一退再退。
我以為婚姻就是不斷的妥協和包容,直到姜芮提出要來我家坐月子,我才幡然醒悟。
這不是家,這是寄生。
我不是妻子,我是宿主。
躺在酒店的床上,我打開了筆記本電腦,開始冷靜地執行我的計劃。
第一步,製造"出差"的完美證據鏈。
我用專業軟體,製作了一份精美的電子版行程單,上面有航班號、酒店預訂信息,甚至還有馬爾地夫當地合作方的聯繫方式和地址。
所有信息都做得天衣無縫。
然後,我用工作郵箱,將這份行程單發給了陸鳴,並附言:行程已定,勿擾。
接著,我用航空公司的里程兌換了兩張真實的、全價可退的頭等艙機票。
一張飛往馬爾地夫,一張飛往國內另一個城市——昆明。
截圖,發朋友圈,配文:"空中飛人的日常,願此行順利。"分組,僅對陸鳴及他的家人朋友可見。
做完這一切,我立刻退掉了飛往馬爾地夫的機票。
那張飛往昆明的,將是我真正的目的地。
第二步,物理隔離。
第二天清晨,我算好陸鳴上班的時間,打車回了家。
打開家門,熟悉的玄關,熟悉的味道,卻沒有絲毫留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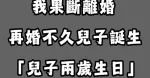
 武巧輝 • 8K次觀看
武巧輝 • 8K次觀看
 楓葉飛 • 4K次觀看
楓葉飛 • 4K次觀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