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平靜地將那張銀行轉帳單放回桌面,沒有一絲波瀾。
七年的付出,八十萬的拆遷款,全部流向了那三個將她趕出家門的兒媳。
大姑坐在沙發上,眼神閃爍,試圖解釋她的「苦衷」。
我只感到前所未有的心灰意冷,我曾以為親情可以跨越一切,但現實告訴我,有些人永遠只忠於利益。
我站起身,俯視著她,語氣平靜得像在談論天氣:「既然她們孝順,就別再來找我了。」
我的話音落下,七年的光陰與親情,徹底畫上了句號。
01
親情債:被遺棄在雨夜的老人
那年冬天,臘月二十六,寒風像刀子一樣刮過臉頰。
我接到鄰居李阿姨的電話時,正忙著準備年貨。
電話那頭,李阿姨壓低聲音,語氣裡帶著明顯的同情和不忍:「小薇啊,你大姑站在小區門口快兩個小時了,身上就一個破布包,好像是被她那幾個兒媳給趕出來了。」
我心頭一緊。
大姑劉芳今年快七十了,身體一直不好。
她有三個兒子,個個都在城裡買了房,日子過得比上不足比下有餘。
按理說,三家輪流贍養,她應該衣食無憂才是。
然而,大姑命不好,嫁的婆家重男輕女,她三個兒子也繼承了這份「傳統」。
他們只顧著孝順岳父母,對自己的親媽卻互相推諉。
我放下手中的餃子皮,穿上外套就沖了出去。
我們家是普通的工薪家庭,雖然經濟不寬裕,但我和丈夫都受過大姑的恩惠。
小時候,爸媽忙,大姑沒少照看我,那份情誼,我一直記在心裡。
趕到小區門口,我一眼就看到了縮在保安亭角落的大姑。
她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舊棉襖,手裡緊緊攥著一個鼓鼓囊囊的布包,臉上帶著淚痕,凍得瑟瑟發抖。
保安小王給我使了個眼色,小聲說:「她三個兒媳婦,早上輪番來送,但誰都不肯讓她進門,說是今年輪到老三家,老三家又說老大家沒盡夠義務。最後,老太太自己受不了,說哪裡都不去了。」
我心裡的怒火騰地一下燃起,但看著大姑那副可憐模樣,怒火又化為了心疼。
「大姑!」我快步走過去,聲音帶著顫抖。
大姑猛地抬起頭,看到我,眼淚瞬間涌了出來,她張了張嘴,卻說不出一句話,只是緊緊抓住我的胳膊,仿佛抓住了最後一根救命稻草。
「沒事,沒事,跟我回家。」我扶起她,她的身體輕得像一片枯葉。
我丈夫張強得知情況後,二話沒說,幫我把大姑扶上了車。
回到家,我給她燒了熱水,煮了薑湯。
大姑這才緩過勁來,坐在暖氣片旁,不停地搓著手。
「小薇,我……我是不是給你添麻煩了?」她的聲音沙啞,帶著深深的愧疚。
我將一杯熱茶遞給她,語氣堅定:「大姑,說什麼傻話。我們是一家人。您放心住下,這裡就是您的家。」
那一晚,大姑在我家安頓了下來。
她的布包里,除了幾件舊衣服,就只有一串磨得發亮的佛珠,和三本泛黃的存摺。
存摺上的數字很小,加起來不到兩萬塊錢,那是她全部的積蓄。
我給她換了新的被褥,她躺在床上,像個孩子一樣,終於沉沉睡去。
而我,卻對著那三本存摺,久久不能平靜。
我知道,這不僅僅是收留,而是責任,是一份沉甸甸的親情債。
02
漫長的七年:付出與旁觀者的冷漠
大姑這一住,就是七年。
這七年里,我的生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我辭去了相對輕鬆的工作,找了一份時間更靈活的兼職,以便更好地照顧大姑的起居。
大姑患有慢性病,需要按時吃藥,每年春天和秋天都要住院調理。
張強是家裡的頂樑柱,承擔了所有的醫療費用和生活開銷,從未有過一句怨言。
他常說:「小薇,你大姑是咱們的長輩,咱們不能看著她受苦。」
我們把家裡的次臥騰出來給她住,房間收拾得乾淨整潔,比她以前在兒子家住的那些雜物間要好得多。
大姑很感激,她總是搶著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務,比如擇菜、洗碗,但身體畢竟是老了,我常常勸她休息。
然而,最大的心病,還是那三個「孝子」和他們的妻子們。
七年間,他們來過我家三次。
第一次是過年,大年初二,他們「組團」來了。
三個兒子,三個兒媳,浩浩蕩蕩地站在我家門口。
與其說是看望老人,不如說是做戲。
他們帶來了廉價的禮品,在沙發上坐了不到半小時,就急著要走。
大兒媳王麗是出了名的精明,她皮笑肉不笑地對我說:「小薇啊,辛苦你了。媽在你這兒住著,我們放心。這不,我們忙,也沒時間過來,你多擔待。」
二兒媳趙梅則更直接,她瞥了一眼大姑身上的新衣服,語氣帶著酸意:「媽,您在這兒被照顧得挺好啊,比在我們家精神多了。」
三兒媳孫燕最愛演戲,她拉著大姑的手,抹著眼淚說:「媽,我們可想您了,但我們家孩子要上輔導班,實在騰不出精力。您在這兒享福吧,我們過段時間再來看您。」
他們每個人都表達了「關心」,但核心信息只有一個:媽在你家住得好,所以我們就不用管了。
大姑看著他們,眼神里充滿了期待,又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卑微。
她小心翼翼地問:「老二,你家上次說換的那個大房子,離我大哥家近不近?」
二兒媳趙梅立刻警覺起來,笑著說:「媽,近是近,但我們那兒是學區房,進出都要刷卡,您住不習慣的。」
那一刻,我徹底看清了這三個兒媳的嘴臉——她們巴不得大姑永遠不要離開我家,這樣她們就可以徹底擺脫贍養的義務。
我沒有拆穿她們的虛偽,只是微笑著送客。
送走他們後,大姑默默地回到房間,直到晚上吃飯時,我才發現她眼圈紅紅的。
「大姑,別想那些不開心的事情了,我們好好吃飯。」我安慰她。
大姑搖搖頭,嘆了口氣:「小薇,你不懂。我不是氣他們不來看我,我是怕他們將來過得不好,沒人幫襯。」
我心中苦笑。
這七年,我們不僅提供了住宿和照料,還承擔了她大部分的醫藥費。
我們才是真正付出的人,而她心裡惦記的,依然是那些從未盡責的兒子們。
這份無私,在我看來,是親情,但在那三個兒媳眼中,卻是我們「多管閒事」和「人傻錢多」。

03
拆遷款的誘惑:八十萬的希望與變數
時光荏苒,轉眼到了第七個年頭。
這一年春天,一個爆炸性的消息打破了我們平靜的生活。
我們居住的這片老城區,終於被劃入了城市改造範圍。
這意味著,我們家住了幾十年的老房子,要拆遷了。
消息一出,整個小區都沸騰了。
我家這套房子雖然老舊,但地段好,按照補償方案,能拿到一筆不菲的拆遷款。
經過詳細核算,我們家可以獲得一套回遷房,外加八十萬的現金補償。
八十萬!
對於我們這樣的小家庭來說,無疑是一筆巨款。
張強激動得抱住了我:「小薇,咱們終於可以把這些年欠下的帳都還清了,還能給大姑換個更好的房間。」
大姑得知這個消息時,表現得比我們還要興奮。
她坐在沙發上,雙手合十,嘴裡不停地念叨著:「菩薩保佑,菩薩保佑。」
然而,從拆遷消息傳出那天起,大姑的言行開始有了微妙的變化。
她變得有些心神不寧,常常一個人坐在陽台上,對著遠方發獃。
有時候,她會偷偷摸摸地打電話,聲音壓得很低,一聽到我們靠近,就立刻掛斷。
我一開始沒在意,只當是老人年紀大了,喜歡安靜。
直到有一天,我無意中聽到了她和鄰居李阿姨的對話。
李阿姨問:「劉芳啊,你家這回拆遷了,可算熬出頭了。這八十萬,小薇兩口子照顧你這麼久,肯定都歸他們吧?」
大姑的聲音帶著一絲含糊和猶豫:「這個嘛……小薇對我好是真,但強子和薇薇還年輕,以後掙錢的機會多著呢。我那三個兒子,壓力也大,買房供孩子,都缺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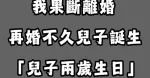
 武巧輝 • 5K次觀看
武巧輝 • 5K次觀看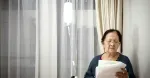
 楓葉飛 • 3K次觀看
楓葉飛 • 3K次觀看




















